发布时间:2023-10-09 17:42:2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对生命美学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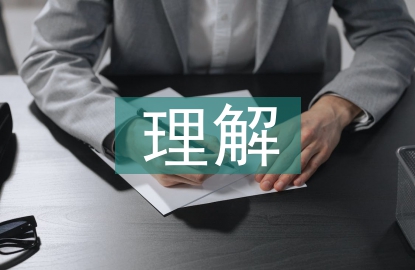
美学在中国,曾经是一个显学,从上世纪80年代后就开启风气之先,成为了中国学界之立独行,勇于改革的一门学科。虽然时至今日,美学已经逐渐有淡出学界的视野,但我们从美学的发展的历史之中回顾这一学科,会发现美学所经历的一场场深有影响的对话。而这些美学对话已经不仅仅的限在这一学科的内部,而是一个时代学界理论范式的转换与创新。
为此,不妨把目光转向了范式理论。范式,是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术语:
指一个特定的时间的特定科学实践者普遍具有的一套假设,它构建一种更大的理论或者观点(比如,牛顿物理学、爱因斯坦物理学)。在社会科学中,这个词语具有很类似的意义。(比如说,在人类学领域,进化论和功能论都是人类学范式。)[1]
按照库恩所说,范式是在其中包含了许多小理论的大理论。当小理论已经不再具有了世界意义,那么危机就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最后会导致某种范式的倾覆,或者作为一个特别的个案,合并到更新更大的范式之中。
我们的话题由此而进入——从“范式”的转变过程来看待“生态美学”的出现。
二、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之论争
中国美学界自从60年代起,就一直是以实践美学为主导。可以说,实践美学是我国2o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两次美学大讨论的重要成果,标志着那时期我国美学的发展水平,而即便在当前仍有其价值。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机械唯物论和传统认识论的时代局限。
而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学界受西方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的影响,产生了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生命美学。生命美学的提出,是“实践美学”理论范式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成果。生命美学的探索之路开始于对实践美学的质疑和批判。潘知常、封孝伦、范藻等学者在肯定实践美学成就的同时对实践美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点直指实践美学范式的要害所在,从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思维方式三方面揭示出实践美学范式遮蔽的问题:
(1)研究对象。潘知常认为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在美学研究中始终未能解决。美学研究明确确立的研究对象有美、美感或审美关系,但不论是以美为研究对象.以美感为研究对象,还是以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都是以一个外在于人的对象作为研究对象,因而都是以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的遮蔽和消解为代价。这样,也就最终地确定了一种对美学的理解方式和对话方式:以理解物的方式去理解美学.以与物对话的方式去与美学对话。而美是审美活动的产物,美只相对于审美活动而存在,只存在于审美活动中。“美是自由的境界”。[2]
(2)逻辑起点。实践美学认为应从实践活动人手研究美、美感或审美关系,提出“美是人质力量的对象化”等命题。生命美学认为应从人的生命活动人手去研究审美活动。封孝伦认为,实践美学忽略了实践的前提:人类的生存。[3]
(3)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潘知常对包括实践美学在内的中国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审查,发现美学研究一开始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即固执地从主客二分的角度出发,来提出所有的美学问题。他认为,主客关系并不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部.只是人类以知识论作为阐释框架时所界定的世界,侧重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外在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必然性的领域的把握。在这种主客关系之中根本没有真正的美学问题.真正的美学问题在侧重对于人类与世界的内在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超必然性的领域的把握的超主客关系之中。从主客关系出发来研究美学将使人在世界之外思考,忽视了人类自身。这样的美学将是“无根
转贴于
的美学”、“冷冰冰的美学”。[4]
而张弘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造成的传统美学的困境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实践美学以这种思维方式审视美学无法摆脱困境,他以人与世界同一的存在一元论拒斥心、物二元对立,以存在论差异原则区分美的事物与美的存在,力主“存在论美学”。
在梳理中我们发现,潘知常从人的生命活动人手侧重于对美学研究中心审美活动的分析,而封孝伦则紧紧抓住生命来建构体系,对生命美学的认识应是把他们作为整体来认识。作为整体,封孝伦对生命哲学作了较完备的阐述,使生命美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哲学基础。潘知常的分析则切中美学之为美学的根本问题。同时.他们对美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美学的思维方式、自由问题等作了重新阐释。将他们的理论进行整合。生命美学带来了思维与话语的双重变革。毋庸置疑,这是一种美学新的范式的变革,当新的理论范式出现后,它所带来的对中国美学的建设性的意义是重大的。
总结生命美学的出现的历程,从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对另谋新路的尝试,带来美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元化。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借鉴更多的西方理论是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更多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哈马贝斯那里吸取理论资源。以主体间性理论、存在美学、此在分析来看待世界;同时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天人合一观、与古典美学对生命的关注对自由的向往相结合来阐释美学。中国生命美学作为多元化美学观念中的一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
三、后现代的范式——生态美学
如果说,生命美学的出现,是在中国美学界面对的,更多是建国后留下的传统思维的禁锢,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那么,二十一世纪初,生态美学出现的语境,面对的是消费社会,全球化的语境,面对着的是现代性的困境。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中,美学界更多心系于整个人类中越来越窘迫的命运,现实越来越强大的压力。
曾繁仁先生在《走向更加深入和成熟的我国生态美学研究》[5]一文中,指出了生态美学对实践美学的继承与超越。
生态美学从坚持唯物实践观的多重角度继承了实践美学,但也超越了实践美学。其超越之处是:(1)由美的实体性到关系性的超越。实践美学力主美的客观性,而生态美学却将美看作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生态审美关系,从而将其带入有机整体的新的境界;(2)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超越。实践美学特别张扬人的主体力量,将美看作“人的主体性的最终成果”,而生态美学却将主体性发展到主体问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3)在自然美的理解上由“人化自然”和“自然的祛魅”到人和自然的亲和与自然的部分“复魅”的超越。实践美学完全将自然美归结为社会实践中自然的“人化”和“祛魅”。而生态美学却承认自然美中自然的应有价值,进行部分的“复魅”,主要是恢复自然的神圣性、部分的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性。[6]
从曾先生的文章,可以很清晰地把握,生态美学这一新的理论范式带来的建设性意义。它对存在论的继承,对实践美学的批判,进一步回应了现实所给出的严峻问题。从现实的环境问题,到人的主体问题,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到人自身生存和存在的问题,生态美学已经脱离旧有的理论范式的限制,走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个方向是具有很强人文意识,现实的关怀感的。
四、共生——生态美学的理论与价值维度
接上所述,其实生态美学要面对的问题是可以简单地简化为三个关系——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解决。这三大关系是后现代问题的一大核心点,特别是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流行的语境里。而生态美学给出的理论维度究竟是如何回答了这些难题呢?转贴于
生态美学有一个很高价值尺度——共生。将共生作为一种美学的价值尺度和理论维度,王尔勃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一观点。[7]“共生”(symbiosis)原是一个生物学术语,指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依生存,对彼此都有利。它是由德国植物病理学家安东·豆·培里于1879年提出的,培里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把“不同生物一起生活”称之为“共生”。国内外学者都已指出,文化多样性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多样共生”既是生物物种之间的一种互利关系,那就也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关系。
在进入后主体性哲学时代,人们并没有否定主体性的意义,而是主张通过“主体间性”完成对主体性的建构和补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哈贝马斯,这种意向越来越清楚。生态哲学作为后主体性时代的哲学,是对主体性哲学的发展与扬弃,但它决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背离与倒退。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是要纠正人类的片面性,而不是放弃认识世界、改造并调节世界这一“自然之子”的责任与使命,更不是否认“自然向人生成”的宇宙进程。
从后现代话语的多声部而言,单一的声音是独语,是霸权。这是不和谐的,并不利于发展。在今天,边缘与中心不断在掀起了一场场对话。边缘对中心的解构不是要确立另一个中心,而是要保持对话。正如,身在中国边缘地区——岭南成为关注的重点。这种关注不是中心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看待与中心相异的他者所在,而是岭南地区自己发出声音。这个声音是由一大批偏居西南一隅,具有文化自觉的学者所发出的。特别是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一大批学者们,他们从关注自身的地域文化,地方传统出发,发扬了岭南文化特有的兼容性,吸纳性,发出另一种声音,使后现代多声部的语义场里真正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达到了互补和谐。黄秉生教授从壮族审美文化研究中总结出了,民族生态的审美范式——依生,竞生,共生。黄教授这三大理论范式,对于生态美学,生态文化的理论视野作出高屋建瓴式的总结[8]。袁鼎生老师溶合了生态学,哲学,美学,明确提出了“生态场”,拓展了生态美学的研究空间,他更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严谨的,庞大的生态美学的体系,为当今日益为工业文明所困顿所挤压的人类社会探寻人类的出路。[9]张泽忠老师植根于自身侗民族的文化土壤,从侗族的歌舞,侗族的建筑,从哲学,美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中去探究了侗民族文化“元语言”,探究了侗民族自身的文化时空秩序,生存伦理智慧,使一个边缘的民族的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出了独特的声音,让世界领略了多元文化之中来自边缘,他者的诗意盎然的文化。[10]这正是后现代精神的启示,从多元中求“共生”,讲究华夏文化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向度。
二、情感化设计的艺术表现
禅宗美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与淡泊超然的人生哲学,能赋予当下艺术与设计实践活动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社会价值。我们固然处在一个哲学概念创新的时代,通过对禅宗美学自然本体论的研究切合当代艺术设计,从全新的角度呈现符合社会意识需求的、崭新的审美形式。在禅宗美学的指导下进行设计,做到自我清净,心中有念,使主体(心灵)与客体(自然)处于同一、恰当的状态下。在这层视野上选择设计所需材质:以简洁质朴的表现方式去达到所要表现物体内在的、本质的、精神的智慧美。禅宗美学自然观追求淡泊简素、朴拙到近乎不完满来表现的美(如图2)。色彩选择应摈弃绚丽灿烂之色,以清新素雅或纯色(白)为主,这种含蓄、清净之色所表达的美感恰恰是最富有魅力,纯真而朴实的。材料应选择天然古朴的木制品或棉麻,甚至是一粒沙,一颗石的美感,呈现出静谧,虚无的审美情趣。这种美是稍纵即逝的,亦是亘古不变的。正如其自然本体论所强调的心性化的自然美感,是由观到感,观中生感,感中生观,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理解,来对自然美的和谐作出反应,从而展现出内在的生命之美,实现人与宇宙和谐统一的诉求。在形态的设计上并无固有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禅宗美学注重“万物归一”的整体观照,即全面地知晓,完整地观察。无论是一幅画或是一件工艺品,都要将其形状、大小及颜色与整体和谐相比较,真正领会它的美。如我们所感受到的自然界事物或风景是美的,不单单是因它独有的形式,更多是因它是以一种创造性的和谐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而使人发现或创造出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和谐,并以此作为欣赏的前提或分析的依据。这样更有助于形成对美和崇高的敏锐意识,从而体验到特定“画面”背后生命韵动的和谐之美。只有如此,对自然生命和人类情感的体验之妙才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从符号学上来说,影像符号可以理解的能指和意指两个理解层面:所谓能指是指电影的视觉影像,所谓意指是指电影影像可能携带着的意义指向。关注能指或是关注意指,其达到的审美作用并不相同,因此将暴力影像区分为两种类型。
暴力影像的两种类型:能指上的与所指上的
(一)能指上的暴力影像
如吴宇森的暴力形象。特点:夸张了暴力中动作要素——动作时间延长,形成了不同于故事时间的特殊时间。在这个故意被放慢的时间里,把武术、舞术结合以来,从暴力动作通常指向的残酷现实中转向审美体验。比如小马哥的形象。这种表达方式与故事(内容)本身的结构和时空秩序无关,而是一种超时空的表现手法,其特殊性在于,它只是在动作符号的能指层面上做了艺术加工,从而影响了观众对动作的审美判断。
再如,昆廷·塔伦蒂诺。他也是通过能指上的突破来达到特殊艺术效果的。一般认为,《低俗小说》在内容上对暴力严肃性的消解形成了玩笑化的风格。在我看来,他把暴力符号的惯常的能指关联加以消解,通过对语境(叙事结构和时空顺序)的特殊处理来转变传统的暴力符号的意义指向,从而达到了对暴力内容的游戏目的。
(二)符号意指上的暴力影像
北野武的暴力影像。特点:与吴宇森相反,动作过程被极度省略,暴力本身作为一个指向更为广阔的生存意义的符号,所以他往往把故事设置在暴力发生点左右,由此得以在生存与毁灭的临界点上展开叙事时空。比如《坏孩子的天空》,小马和新志。在北野武看来,极端境域才能激发生命意志,意义才能在生活中燃烧起来,暴力世界正是这样极端体验的引导者。暴力本身不引起审美判断和道德评价,而是暴力所意指的那些生存境遇,让我们得以判断。
必须指出,无论是在能指层面还是在意指层面,暴力符号在审美判断上的暗示往往带着强烈的道德诱导,因为我们的日常语言往往把美和好一起使用,仿佛美的就是好的。郝建先生因此提出了“美学暴力”和“暴力美学”的概念①。暴力美学真是对美学暴力的彻底的反驳,因为他“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了观众”。但如果说爱森斯坦是把意识形态强加给观众,是导演意识的霸权,那么吴宇森让观众在银幕上体验到暴力行为的诗意,奥利弗让天生杀人狂变成救世主而得到观众的理解,难道不是审美判断对道德判断的诱引?无论是能指上的或者意指上的符号都不可能脱离作者的叙述立场,关键在于在作者意识形态的同时,暴力符号是否给出了合理的意义引导,是否给我们展示了更为深层次的意义世界。如果只是暴力影像,那这等于是在蔑视电影的存在。
暴力符号的审美判断和意义指向
电影中的暴力符号之所以被人们关注,正是因为它并不是作为现实的暴力行为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指向更为宽广的意义世界的符号,那么,是什么样的意义世界呢?
(一)对暴力影像的审美判断:丑恶与不好看
对于暴力现实,往往人们会说丑恶。黑格尔认为:“丑更与内容有关”②,即一个在现实中被认为是丑恶的东西被艺术创造得太好了,在艺术中就是美的,因此“丑”也是一个审美判断。拿暴力影像来说,丑能够描述的只是暴力影像所对应的现实情景,当这个情景在艺术中展现出来,就是属于审美判断了,与现实的“恶”无关。比如,当富有舞美的暴力影像产生震惊的审美效果并引领着我们进入审美之境时,艺术早就从我们心里抽离了现实经验中关于暴力行为的丑恶判断,剩下的只是审美愉悦。同样的,当北野武通过暴力形象将生活推向了生与死的临界点时,生活的困境在暴力的舞台上豁然展现,丑恶的判断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故事内容唤起了观众的生存共鸣。
除了丑恶,我们还有一种审美判断——“不好看”。不好看可能带给我们两种不同的感觉,一个是丑感,一个是痛感。引起丑感的“丑”,一般是艺术家为了表达特殊审美意味。比如,庄子笔下长着肉瘤的人,他一开始带给人们的是丑感,但却被庄子审为“美”人,其目的是为了表达接受自然就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痛感则更与崇高有关。崇高的本质特征是对立,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巨大异己力量压抑下的张现和高扬,尼采将它描述为酒神精神,认为它促使人感受到生命的强健。而帕特里克·沃尔的《疼痛》③认为,痛感的激发会刺激到原本无意识的领域,使其成为意识,即心灵的活动参与了进来,于是就有了反思,有了意识的诸种活动。就北野武的影片而言,当导演通过暴力境域把主人公的生存矛盾全面展现出来时,观众往往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主人公的生存痛苦,进而就产生了认同。
那么,电影中的暴力符号所激发的审美判断是如何影响了观众理解故事所展开的生存境遇的呢?
(二)否定、反抗与人性热情
尹鸿先生认为暴力影片存在的作用就是宣泄,也就是说观众被压抑的暴力欲望释放了,因此得到了。这个说法显然与弗洛伊德有关。
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④认为,生命被两种本能所控制——死本能与生本能。生命本能(力比多)导致新生命的诞生,使人类的生生不息。死本能则是人类的血液中留着嗜杀的欲望,是暴力、凶杀、自杀。生本能和死本能构成了人性的张力。虽然这个理论要解释的是现实中的暴力行为,但他强大的解释力对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艺术不仅表现了这个压抑与释放的过程,而且利用绝望的悲观情绪和生存底线来激发起人对自身意义的追问。电影艺术往往就借助了暴力作为一种否定的抗争力量,来展现人性的极端处境,从而达到对人性的拷问。
比如《辛德勒的名单》《战马》等大量描写战争的影片,往往把爱、同情和信仰等人性的超越性价值作为对抗着暴力所带来苦难的力量,通过否定性的因素而变得感人至深。这种对抗式的表现手法在罗贝尔托·贝尼尼自编自导自演的《美丽人生》中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影片用诙谐的方式把基多对生活、对妻子和孩子的爱表现得生动有趣,在欢乐中把纳粹的统治凸显为抗争暴力的力量,拉大了对抗的张力,从而凸现出了基多所代表的人性中至美至善的一面,成就了一位超越战争暴力所带来的绝望命运并守护着至纯心灵的崇高形象,在解救了自己的孩子的同时,也仿佛成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基督(与基多谐音)。
此外,弗洛姆修正了本能理论,通过把弗洛伊德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修正为爱与破坏,提出了人性热情的概念。弗洛姆认为本能纯粹是自然的产物,而人性热情则是社会的、生物的与历史的产物,因此它可能产生两种破坏性:良性的和恶性的。弗洛姆认为:“如果人要得到广泛的解救,就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把人重新放回到崇高的地位上去。……这样的社会能够动员人类对生命的爱,而有对生命的爱才能打败主对死亡的迷恋。”因此,他一方面同弗洛伊德一样在人性层面给暴力找到了位置,另一方面却把对暴力的研究指向了对人的本质力量和超越性的呼唤。正如《美丽人生》中的战争和残酷的描写,一方面刺激了观众在现实生活的痛感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像基多这样超越痛苦的崇高形象,唤醒对生命的希望,在两种对立的情绪中使得人们进入崇高的审美之境。再如吴宇森电影中的小马哥形象,这位传统意义上的黑帮分子,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勇气,通过他挥抢扫射时的潇洒,展现的正是一个至纯至性的英雄义士的形象。
当然,《天生杀人狂》和北野武影片中的暴力影像不同于基多,也不同于小马哥,他们往往是破坏者,是弗洛姆定义的恶犯者(人类特有的毁灭性向和绝对控制欲)。米基和梅勒认为,既然你还在世界上接受痛苦的磨难,我就要拯救你,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去一个纯洁的地方,死亡就是救赎。这意味着,用暴力毁灭他人肉体是为了来救赎他人的灵魂,所以杀人狂本意是种救赎热情。在这个看似变态的逻辑下,我们可以追溯到问题的核心: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人们需要拯救。这个被反抗的世界是一个精神萎靡,以近乎原始的霸权和力量主宰的世界——谁能杀人谁就有力量,谁就可以生存下来,这也就是《大逃杀》里所隐喻的暴力世界。所以,影片中的以暴制暴就是否定和破坏现有世界秩序,以达到拯救。奥利弗·斯通的社会批判性正在于此——塑造了一对寻求拯救的杀手,他们要杀死的是肮脏的世界。
弗洛姆认为“人性热情把人由物体变为英雄,使他虽身处巨大的障碍之间,仍想使生命有意义”⑤。生命的意义,是暴力与死亡的终极指向。比如,吴宇森把小马哥这样一个反叛角色用忠肝义胆正面英雄形象来塑造,正是通过对这个社会正义与邪恶秩序的拷问,对黑白经纬分明的道德判断的挑战,来呼唤人性的本质力量。通过对现有观念的摧毁达到对真正人性的张扬。在北野武那里,自身拷问式的暴力和死亡是一种自我施暴,以示抵抗现有的生存处境而达到拯救。如弗洛姆所言,人性热情正是人使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完整的人的原动力,而完整的人始终是面对生存与死亡的。这种保持整全的方式在艺术中表现为救赎心态。无论是对他人社会还是对自身,暴力都是以暴制暴而获得了新的理解,其实质是通过否定他人或者自身的肉体而达到对生存强烈体验和追问。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纠结的方式: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消灭生命。这不免让人想起弗洛姆所说的真正的倒错,“生命为使自己有意义而跟自己敌对”。
因此,无论是《天生杀人狂》、北野武的暴力影像或者小马哥,无论是能指上或者意指上的暴力符号,它们作为电影符号的意义并非指向暴力行为本身,而正是弗洛姆所呼唤的人性热情的艺术表达——暴力一方面提供了人们面对生存或是毁灭的境域,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展现和高扬生命本质力量的舞台,在这个互相角逐的生死境域和人生舞台上,演绎出的是对绝望的抗争和对希望的渴求,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表达。如果说,暴力符号作为对生存与死亡的隐喻,无论这个毁灭和绝望指向社会还是自身,无论是用理想人格来超越它还是用它来批判社会现实,它都承载着丰富的内涵成为艺术世界的一部分,成为审美对象,并获得了丰富的美学价值,暴力美学的含义也当于此。
注释:
① 郝建:《坏孩子带来的思考——暴力美学源流论》,《成言艺术》,2002年2月号;《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杂耍蒙太奇新论》,《当代电影》,2002年第5期。
②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页。
③ 帕特里克·沃尔:《疼痛》,周晓林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二章,疼痛的哲学”。